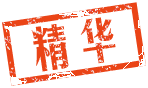|
蜕变
(一)
我又无端做了这种梦—到处逃,解救我的仍是一束光。我慢慢睁开眼,是阳光。我翻过逃出梦的身体,左手摸起身旁的手机,显示着“2020年8月1日,星期六,10:00,巴塞罗那”。十点了!时间总在休息时变快。我快速起身,穿好衣服和拖鞋,习惯性看看窗外楼下:跟每天早上一样,每个从梦里醒来的人,都重新支配自己的肉体,忙碌苏醒的精神,为了让时间变得更慢。而许多时候恰恰相反,精神越是忙碌的时候,肉体的时间也变得越快,比如考试或者谈恋爱…
“停!”—我把自己从思想的“黑洞”边缘拽出来,否则又是“撕裂”的一天。接下来的我,就像个机器人:洗水杯,烧热水,洗烟缸,给阳台晒太阳的乌龟喂沙拉菜,给阳台的几内亚花喂水,数一数开着的几朵花。然后歪到电脑前的椅子上,吸根烟,等水开,对着眼前黑屏发会呆。水开后,倒进保温瓶还有水杯,然后洗漱。接着,靠到沙发床上看手机新闻。手机,这个二十一世纪初大量吞噬人类时间的“怪物”,更像病毒一样感染精神领域—试图长期与人类共存。
对于毫无成就的平民,这个“病毒”会让人忘记与它保持“距离”,成为“无症状感染者”,就像我。今天的阳光很温暖,我感觉会有好消息,比如“找到新冠病毒的源头”,比如“病毒疫苗已研发成功”…足以让我高兴到明天。
我充满期待的打开新闻页,第一条:“2020年7月31日讯,根据《西班牙人》的报道,西班牙极右党派领导人日前,在西班牙议会全体会议上,就新冠病毒疫情大肆攻击中国。据介绍,西班牙‘民声党’领导人一贯以‘中国病毒’,‘武汉病毒’等标签化的方式,来称呼新冠病毒。此次在会议上,更是将矛头直指中国,大放厥词…”。
我关上手机,没有再看第二条新闻。站在阳台上,望向几公里外那一点隐约海水的蓝,静止的,精致的,像一块蓝宝石,永远在几公里外闪烁,随时在等着和我对视。我却永远够不到“它”,更加永远得不到“它”,因为走近了,它就不是“蓝宝石”,或许会变成一片浑浊。我习惯放下帷帐,挡住阳台从别处来的视线与阳光,那样我会觉得更安全,至少会阻挡我从七楼跳下去的想法,那个奇怪的想法,就像恶魔一样缠着我,每当我走上阳台就会出现,总会让我手心里冒汗。
事实上,我总是从帷帐的缝隙,不被外界发现的偷看“蓝宝石”。那感觉,就像打开一个属于我的宝箱,然后我的灵魂与宝物融合,忘记人类社会所有的事,尤其关于意识形态,种族,政治,文化等,因为一张东方面孔而引来的那些“生而有罪”的麻烦。
这一次,我看着“蓝宝石”,却浮现许多忘记的事…那些事就像在一个水晶球里面,我在外面默默地看着:一月到三月之间,我面前路人们的眼神,像五线谱里的休止符,更像足球裁判的哨音,尽管我尝试低着头走路避开任何人与他们的目光,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一股气场,比如迎面距离二十多米的路人,会下意识穿过街道走另一边,留给我的路畅通无阻…
一阵清新的风,吹醒阳台的我。因为那条讨厌的新闻,我又看了“蓝宝石”好久,只觉得两条腿有些酸。身边更有几只苍蝇让我无法继续回忆,它们总喜欢不合时宜的刷存在感,到处打破人类的平静,让人与它们一样,找不到一处安身之地。更把人变得躁郁的是,今年苍蝇蚊子特别多。
我很羡慕脚下的乌龟,在塑料壳围城的家园,尽情享受阳光与午餐,自己还有躲蚊蝇的壳。每次吃饱以后,它就想爬上塑料壳围的“城墙”,那是我和夫人给它的家园,它却总觉得是个监狱。它用餐的时候,不会在意有我的存在;它饱餐后,总想爬上“城墙”逃到看得到却触不到的地方,它以为那里有更多的食物与自由;它爬不上“城墙”的时候,总喜欢抬头与我对视。我知道,它想让我帮它逃出去。它也许想:既然可以从我这里获得食物,为什么不可以获得自由?因为它不知道,“监狱”的管理者就是我。
就像我不知道,谁是我的管理者。可是我总意识到被管理,因为我总在想逃出去,却不知道“城墙”在哪里,更不知道该往哪里逃。然而,我总觉得压抑到窒息,那个管理者无处不在,他甚至就藏在我心里。我能感受到他建立的无形而随身的让我与外界隔离的围墙,我却永远无法看到他。每个人都被这样的围墙所困,都不得不慢慢适应它。 也许,就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面瑞德的一段台词,“这些围墙很有趣的。开始时,你恨它们;而随后,你适应了它们。你开始离不开它们,那时候就是被体制化。”。
我们都把管理者当成恩人,同时也把他们当仇人。人们都向管理者乞求,当一个人乞求的时候,被鄙视总多于被怜悯;人们还向管理者抗争,当一个人抗争的时候,被欺骗总多于被妥协。而最后他们没有输赢,因为彼此都囚于体制的墙内。我不想把乌龟与我变成祈求者或者抗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,而事实却不得不如此,它乞求食物抗争自由。我给予食物限制自由,美化成保障它的安全。
乌龟只拥有自然属性,我比它多了社会属性,我的“监狱”是无形的。人类实际上感觉“监狱”和“自由”的是意识,不是客观存在的身体。比如囚犯被关在监狱里面,而狱警—囚犯的管理者也在监狱墙内,他们只是比囚犯多一些空间。囚犯会觉得没有自由,因为他们意识里属于“被管者”;而狱警却觉得有自由,因为他们意识里属于“管理者”,刚好管理囚犯的自由。
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在社会里的诠释与体现。人权的社会属性,平时会与自然属性和平相处。在疫情封城时,国家的管理者取的是生存权,舍的是公民自由的权利,偏重自由的人就会因此抗抑,忽视社会属性的责任。实际在任何空间尺度,有肉体容身之所就有自由,一米与一公里的活动范围,拥有同等的自由与不自由,关键取决于意识本身。当意识认为肉体的活动范围被自我意识管理,就是自由,反之则否。疫情时,人类为实现自然属性的抗争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属性的存续,比如西方国家的许多公民。
所以,当西方国家正攵府想要封城时,许多喜欢平时就呆在家里的人也会觉得自由被束缚,因为被管理就是一种“监狱”,意识才是真正的囚犯。有人说地球就是一个监狱或者是一个试验场地,由高等文明管理人类,只是人类无法感觉到。如果确实如此,不知道就会比知道幸福得多。因为知道以后,人类会觉得没有未来与希望,命运都被外星人管控,即使再多的自由,也等于没有自由。
然而在发现外星人以前,人类还要继续相互倾轧生活在种族相互纠缠的世界,生活在意识相互摩擦的人间。这一点,在外国的中国人,与在中国的外国人也许感受更深。他们更有相同的感悟:包容是唯一共存之道。然而在疫情席卷世界的时候,包容就不会那么容易。
从疫情开始直到现在,那么久没有看到曙光,人类社会已经疲惫不堪,人们变得越来越躁动。我已经不期望被包容,只有努力减少出门的次数,把自己孤立起来,感觉世界还是温暖的。自闭久了,我的社会属性还是想让我回归人群。我不得不从身体自由空间被挤压的小“监狱”,回到意识自由空间被挤压的大“监狱”,不管有无包容,一米或一公里,只要看到人就好。每次迈出家门时,我都决意面对一切外界烦扰。然而实际上,我总像狮子一样思考,像豪猪一样行动。
【温馨小贴士:点击只看该作者即可在帖子里连贯阅读】
|